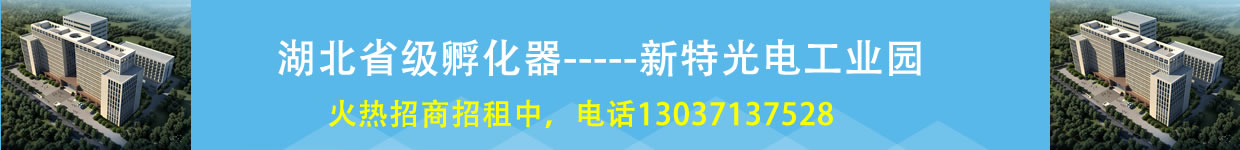风云岁月--陈昌炎自传(2)
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
五代单传
公元1940年7月20日(农历六月十六)午时,我降生在一个只有两间破茅草屋的家庭。这里是湖北省公安县三根松东北端的公兴大院,它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支流——虎渡河畔,自然条件十分恶劣。每到盛夏时节,如果连降几场暴雨,上游滚滚而来的洪水就蓄积在这里,成为一片汪洋。民间流传说:低湖田,雷喊坵,十年就有九不收,养女若嫁公兴院,一生一世受苦难。
我的父亲陈吉贵,生于1901年。祖父陈永柱中年患病,因家境贫寒无钱医治,41岁就去世了。父亲从小就挑起了生活重担。虽然他一个大字不识,但人非常聪明。农村的竹木活、纺纱织布、打渔熬糖、轧花打米等各种活路他都会干,而且工艺精湛。性格开朗,为人忠厚,在村里人缘极好。农闲时每到晚上,乡亲们就到我家聊天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。
遗憾的是,父亲的前妻周氏,年过三十只生下一女,名昌珍,入祝门生一子祝方彬。因父亲这一门五代都是单传,所以把子嗣看得比什么都重,于是就同周氏解除了婚姻,娶了我生母邹苏嫣。生母生于1915年,小父亲14岁,湖北省石首市新厂镇横沟市人。早年她曾在横沟一带组织“女子农友会”,协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。1939年日寇攻占沙市,江北受到威胁,她逃难到公安县沙口市。母亲生下我不到半年,不幸身染重病,花费了家中所有积蓄,多方求医,终因医治无效,于农历1940年腊月十八日,撇下只有半岁的我,撒手人寰,年仅25岁。母亲的早逝,对不惑之年的父亲,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他忍着悲痛,抱着嗷嗷待哺的儿子,满村给我找奶吃。可是我拒绝吮吸任何人的奶水,即使强把奶头塞在嘴里,我也要吐出来。这真是愁坏了我的父亲。没办法!他只好东家讨西家借,把米磨成面粉,熬成糊糊喂我,勉强保住了我的小命。那时的我瘦成皮包骨。父亲为了我什么事儿也不能做,既当爹又当娘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常常尿湿裤子无人知,肚子饿了只会哭。哭累了睡,饿醒了又哭。俗语说得好:宁跟要饭的娘,不跟做官的爹。男人毕竟是男人呐!母亲的胞妹苏宜珍得知我的情况后,不顾路途遥远,多次给我送来食物和衣服,往返一次需要三四天时间,而且她家里要喂养几个表姐妹。
为了抚育我这颗独苗,在众人的劝说下,父亲终于横下一条心,为我娶回继母雷氏。
刚到六岁,父亲就送我去读书。这是公兴垸唯一的一所私塾,学堂设在干姐邓元秀家。启蒙先生叫甘其源。我小时的记忆力特别好,三天时间就把“三字经”给背诵出来,深得私塾先生的赞许。
1949年,公兴垸遭暴雨袭击,整个垸子成了一片汪洋。我只好被迫中断读书,开始帮父母亲干家务活。这年腊月三十,家家忙着过大年,我家却肉无半两,鱼无一斤,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一粒。怎么办?我邀上邻居伙伴易继春,说:“咱俩到外边讨饭去!”于是,一人背一个袋子,拖着一根棍子,出门讨米要饭去了。我俩来到崔家大院,被一条恶狗追撵。我们哪里跑得赢它!恶狗咬住我的左腿,咬得鲜血直流。米没讨到一颗,带着空袋子,拖着那条血淋淋的伤腿,一跛一颠地回到家里。父母亲围着我痛哭了一场。这件事被我干爹知道后,赶忙送来一些米面,这个年才得以过去。
胆大少年
小时候,别人说我“天不怕,地不怕,惶横胆子大。”其实,我也有怕的时候。我最怕的是隔壁的断腿甲爹。听人说他中年时,因脾气暴躁,被人打折了一条腿,从此后就拄着一根拐杖走路。他独身一人,住在一间小茅草屋里,靠编竹活为生。他看人不顺眼就骂,小孩子学他走路就追着打,一副凶像。大人不缠他,小孩躲着他,我一见他就害怕,一般都避过他的视线走开。因为住的太近,有时高兴了,他硬要我过去陪他玩。要是不去,大人会说我不尊重老人。所以每次去,我都是战战兢兢地靠近他。
有一次,一个年轻人匆匆走过来,对着断腿甲爹直问:“嘿!沙口市还有多远?”甲爹手里编着竹活,头也不抬没有理他。那年轻人连问三遍,老人还是没有吭气。我以为甲爹没有听见问话,正准备告诉那个年轻人。这时甲爹的锐利目光,扫了我一眼,意思示我不要搭理。年轻人以为老人是个聋子,便拉起老人的衣服问。老人漫不经心地说:“你问我呀?还有一千多丈吧?”年轻人说:“你这里讲丈不讲里呀?”老人怒气冲冲地说:“你说哪个牛鸡巴日的不讲里(礼)!”年轻人自知失礼,调头就走了。那个年轻人不过是缺乏礼貌,冒失了断腿老人,形成一种紧张、对立的关系,给自己带来不愉快。我目睹事情的全过程,使我对甲爹产生了敬畏。我感悟到年轻人问路、说话、办事,一定要谦虚、谨慎,对人要有礼貌。不能口吐狂言,傲慢待人。人不可貌相,良师益友往往来自不起眼的平凡生活中。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,影响很大。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,首先要尊重别人。我也常常用这件事告诫自己的后人。
我小时候真是又调皮,又贪玩。家里穷得常常吃不饱肚子,我依然生活得很快乐。记得解放前一年,和私塾同学课外之余,用仅有的一个黄铜角子甩洞、丢叉。就是在前方约6米处挖一个圆洞,或竖起一个小三角架,参加比赛的人站在规定的位置,用黄铜角子丢过去,或者用挖野菜的铲子甩过去,要是黄铜角子丢进了洞,或者是铲子把前方的三角架打倒了。谁这样做到,就算谁赢。我呢!丢黄铜角子或甩铲子,都比较准,十有八九赢。就是现在三到四米以内,我基本上都能击中目标。这项技能可能是那时候练就出来的。做这些游戏,起初是赢者打输者的手板心,后来挖野菜时,就用挖来的野菜赌。有时候挖来的一篮子野菜全输光,有时候赢几篮子野菜。赢了的就坐在那儿玩,输了的赶快去挖。没有野菜带回家,就要被打或者挨骂。所以我们经常挖野菜到天黑才回家。
我最喜欢和隔三家的万其同学玩这种游戏。因为他是万家大少爷,家里有钱,输得也很干脆,一般都能兑现。有一次,我在万其同学家玩,看见他父亲手里拿着好多白花花的大白角子(银元),我蛮想有一个。万其说:“我家里还有好多白角子,这样吧,我们俩人来丢洞,要是你赢了,我就给你拿白角子来。要是你输了,就天天给我做作业。”于是我们俩就在他家门前的稻场里,挖了一个特别小的洞,小得几乎只能把铜角子滚下去。万其又说:“以三次为一回合,要是连续三次将铜角子丢进洞,就算赢;连续三次丢不进去,就算输;连续三次丢进了一次或二次,算不输不赢。重新再丢。”万其没有丢进一次,我连中三个回合。这样,万其输给我三个白角子。可是这次万其不守信用,他耍赖不给。之后我多次找他讨要,他继续耍赖不给。他一会儿说他妈管得紧,拿不出来,一会儿又说等他父亲回来,喝酒高兴时要钱。转眼到了腊月间,我跟他翻脸了:“你不给我,等到正月初一去找你父亲要!”
1949年的正月初一大早,我悄悄从家里溜了出来,去万其家要白角子,他父母亲都在南面的屋山头晒太阳,他父亲见我走过去,对我说:“享儿!(因我父亲39岁得一子,所以给我取乳名叫享儿)这早就来拜年啦!”
“不是的,我是来找万其要白角子的。”我说。
“什么白角子?”万父问。
“万其欠我三个白角子,是在您家门口丢洞输给我的。”我将事情原委告诉他。
他父亲大吃一惊!忙问他儿子万其:“是怎么回事?你们胆子不小呀,还赌起银元来了!”
万其有口难言。我一个劲儿地要。万其父亲转脸大笑起来,调侃地说:“初一有人要帐,必是消灾之事,折财免灾喽!”然后要万其妈进屋拿出三个白角子给我。
我手里拿着三个白角子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!我又蹦又跳地到处展示给别人看。乡邻们听说后大吃一惊,反倒为我担起忧来了。有的还戏说我“天不怕,地不怕,惶横胆子大,敢找大哥把钱拿。”所谓“大哥”即土匪头子。这件事被我父母亲知道后,更是大惊失色,拿着棍子到处找我,主要担心我遭暗算,全家人紧张得不得了。找到我后,父亲忙请人领着我,拿着那三个完好无损的白角子,忧心忡忡地上万家门去求情。父亲当着万其父亲的面说:“享儿,跪下!”强令我赔礼道歉。我不服,大声地说:是万其欠我的,凭什么要还给他?没门!我一回头就撒腿跑掉了。
后来听说,万其的父亲始终没有收回那三个白角子。后来又听说,父亲将这三个白角子交给我干爹,还买了些礼品送到万家。我感到这个春节真倒霉!三个白角子不但没有得到,反而是在挨打、被骂和恐吓中度过。
好在这一年解放了。6月份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,收复了沙口市。万其父亲的兵力和武器,全部投降缴了械。
1955年春荒时节,一天下午,母亲让我到乡政府领救济粮支拨证,我家离乡政府来回约40华里,天黑前我赶到了乡政府民政办。负责发证的办事人员外出,我等了一会才领到。返回路上已进入深夜,天又下着毛毛细雨,伸手不见五指。完全凭着我对路况的熟悉,慢慢地摸着往前走。这一段路约有一半是起伏丘陵、岗坡坳地,还有大竹园、长树巷,人烟稀少。村里人都说我的胆子大,但这个夜间一个人行走,还真有点恐惧!3华里长的大竹园旁,一条小路蜿蜒曲折,漆黑的夜间,万籁俱寂。快走出大竹园时,看见远处似乎有一个小棚,棚内还有幽闪的亮光,使我本来害怕的心里,更加紧张起来。我强作镇定看了一会,确信是个棚,棚内有亮光。我又蹲下来,擦了擦眼睛,再仔细看:那幽闪的亮光旁,像有一个鬼在不时地点头。这时,我的大脑里发出紧急指令:“没有退路,只能前行,赶快作好自卫准备。”我迅速从竹园里,拉起一根小竹子当武器,接着开始大声唱歌,为自己壮胆。这时候,我似乎感觉到前后左右,都有鬼向我逼来,紧张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,棉衣也不知不觉被汗水湿透了。在距离棚子大约10米处,我停下脚步,看见蹲着一个老头,端着长长的烟杆在吸烟呢!
我大喝一声:“你是谁?干什么的?”
“我……我是要饭的,走在这里天黑了下来,又下着细雨,没有人家,就想在这里度过这个黑夜。”
我的天啦!还真是个讨饭的老头。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白天走过时,没有发现有这个小棚,怎么回来有了呢?原来我经过之后,一位难产妇女死了埋在路旁。还搭棚夜间亮灯一周,以示留念。
再往前就要走下陡坡、走坳地,还要经过付家桥,又有约4华里路没有人烟。我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。刚才的难产棚、忽闪的灯、讨饭的老头,渐渐地消失在夜幕中。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老人讲过的,日本鬼子在这里滥杀无辜的情景,在这一片土地上,掩埋着100多条人命呵!想到此,还没有完全平静的心里,又开始突突突地紧张起来……走过一段长长的低谷,再往上走,开始听到狗的叫声。猛然间,我感觉全身冰冷,撒腿往家跑去。
母亲问我:“怎么这么晚才回来,我们担心得不得了?”母亲一边问,一边帮我脱棉衣,看到我的棉衣拧得出水来,反而使母亲大吃一惊。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
1950年,我进了沙口市国立小学,1954年荆江分洪,原沙口市小学迁到一公里外的三根松山坡上,改名三根松小学。在那里读完了六年制小学。我在学校里,成绩优良,从三年级起担任班干部,一直到毕业。1955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、学生会主席,同时被少先队保送到共青团,成为三根松小学年龄最小的共青团员。和班主任陈常超、教导主任罗月陔一起,组建孟溪区三根松小学师生混合团支部,推举我担任团支部书记。
荆江分洪时,我家搬到了“仙女台”,盖了两间茅草屋。因劳累过度,父亲的支气管哮喘越来越严重,基本丧失劳动能力。母亲是小脚女人,干不了重体力活。繁重的家务劳动就落在我的肩上。仙女台地势高,饮水困难,一口井也没有,必须到很远很远的堰塘去挑水。我每天一亮就起床,挑回三担水,再把娘洗过的衣服拿到堰塘里去清洗,然后才去上学。做完这些活得花三个多小时。从家里到学校,中间隔着一个文家湖。平时人们到三根松赶集、学生们上学,主要靠摆渡。当时我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,哪有钱乘船过渡?所以,我只有绕着文家湖,步行到六华里外的学校。路上最快也得需要半个小时。这样,每天的早操和朝读,我无论如何也赶不上。因不能按时到校,曾受到老师多次批评,也罚过站。老师询问迟到原因,我总是环顾左右而言他,不愿把困难说出去,并努力争取不再迟到。尽管我每天紧赶快赶,可是,有一天我还是迟到了。当我来到教室门口,喊了几声报告,老师像没听见似的,拒不开门。我只好扒在教室外边窗台上,听了一节课。下课后,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让我解释迟到原因。我无奈地向他说出了真实情况。老师听后当时眼睛就湿润了,严肃的面孔慢慢变得十分温和,他说:“以前老师不了解情况,对不起!以后再迟到了,放学后就到我这里补课吧。”还将我的情况向全班和学校作了通报。从此,我得到学校和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,有的主动上门给我补习功课,有的同学干脆陪我一起跑步上学。
每到假期,我要到远地去砍柴,下湖捞鱼、挖藕,挑野菜。1952年,国家在黄山头建设荆江分洪节制闸,集中了上万的建设工人。我把每天捞的鱼、藕和砍来的柴,挑到那里去卖,再换回食盐、火柴、煤油等生活用品。我家离黄山头工地比较远,每天半夜就起床出发,饿着肚子赶路。
有年冬天特别冷,湖面结着厚厚的冰。我跨过虎渡河,来到黄山镇谭家湾渠捕鱼。用细绳编织的约八平米的正方形渔网,四角用竹竿绑成的十字架吊起,十字架中央系上一根粗绳,再立一个三脚架控制粗绳的升降。这样渔网可随时入水或吊起来。我站在岸上,定时将渔网从水里拉出来,河里的游鱼落在网中,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我在河边整整待了两天两夜,忘记了饥和寒,一共捞起了200多斤,清一色的鲫鱼。我用这些鲫鱼换回了80斤大米,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似的。
1954年荆江分洪,我的家乡成了蓄洪区,全家生活靠国家救济。有一次需要先到乡政府领取救济粮支拨证,再到章田寺粮店去买米,来回有百把里路。父母亲当然不放心我去。我毕竟有了14岁,望着多病的父亲,和小脚的母亲,为了全家人的生活,我必须去!
北风呼啸,漫天飞雪。在父母亲的叮咛声中,我上了路。回来时我背着30斤救济粮,起初还走得蛮快,慢慢地、慢慢地越走越慢了。肩上的粮袋越背越重,30斤好像成了50斤,甚至比一百斤还重。我在崎岖的山路上,一步一颤,踉踉跄跄地奔走着。望天空浩渺无穷,看大地一片苍茫。何时能走到我的家啊?我瘦弱的身躯,被沉重的米袋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,雪水浸湿了我的棉袄。体外又罩上一层薄冰,像穿着一身盔甲。三步一停,五步一歇。路面已经结冰,踩在上面滑溜溜的,随时都有滑倒的危险。有几次险些摔下山坡。最后几乎是一步一挪,一步一挪地往前移。回到家时已是深夜,我真的累坏了,饭也没吃就一头倒在床上,睡了一天一夜没有睁眼,没有翻身。事后庆幸自己,终于把30斤大米运回了家。
1954年荆江分洪。这年深秋,滔滔洪水虽然退去,家境却一贫如洗。为了改善贫困的生活,我跟着人家去本县黄水套砍芦苇。父亲告诉我,姨妈就住在江北的石首县新厂镇附近,与黄水套一江之隔。这一年我14岁,由于力气小,加之芦苇根深、杆子坚硬,我不是割破手,就是砍到腿,双手双腿弄得血淋淋的。此时我想起了临走时父亲的交代,便放弃了砍芦苇的活,渡江去新厂寻亲。经过多方打听,终于在红旗村找到了姨妈家。姨妈见我一副寒苦的样子,心疼得眼泪直往下掉。连忙请来裁缝给我做衣服,又给我杀鸡、捞鱼、买肉,做了好多好吃的菜。可是,这些菜都放在灶台上,始终忘记端出来。就着桌上的两碗剩菜,极度饥饿中的我,哪管什么好菜歹饭,只管埋下头去,狼吞虎咽往嘴里扒。姨妈坐在我的对面,充满怜爱的目光盯着我看。突然姨妈叫了一声:“唉呀,心里好难受!”我急忙丢下碗筷,把她搀扶到床上躺下。只见她顷刻间口吐唾沫,不省人事。过了一会,又用我妈的口吻说了很多关爱、挂念我的话语。一时间弄得我和德钦表弟束手无措,不知如何是好。慌忙跑到村里哭喊大人们过来帮忙。后来听人说,姨妈犯的病叫“捆童”。我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,但我知道姨妈思念我这个姨侄,早已成为她的心病。
1955年,我小学毕业,接着考上了公安二中。为了供我上初中,母亲起早贪黑,拼命地做活计。我小学的班主任陈常超,还有易伯阳老师,千方百计地资助我读书。可是,家里的生活完全没有来源,父母身体每况愈下。可怜的父母亲,再也供不起我读书了。入学不到二个月,我只好挥泪告别了学校,告别了我的学习生涯!回到公兴村,成为最年青的社员。